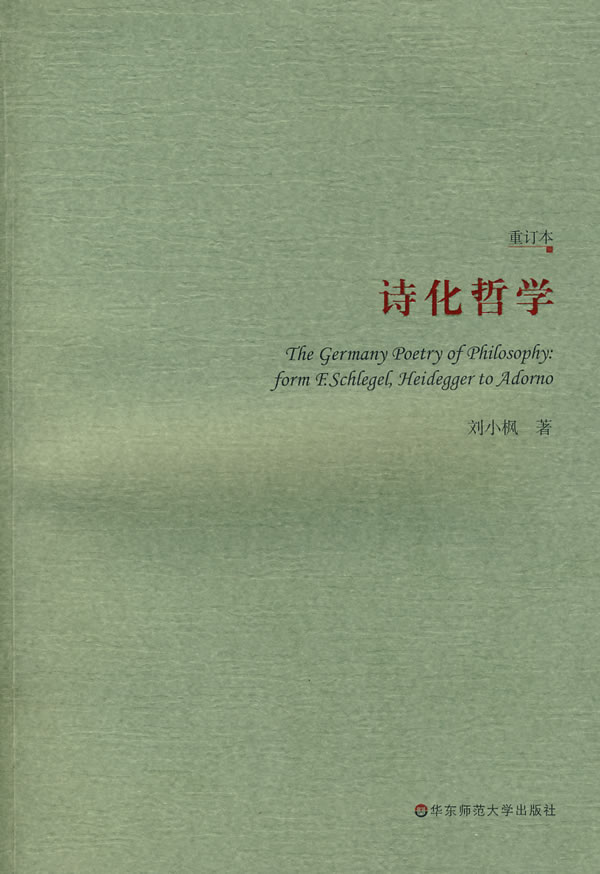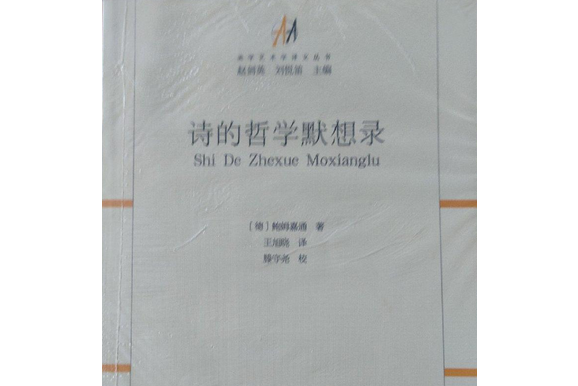奇迹与“微物之神”/黄舜
探索“现实生活背面”的诗学/宋云静
重生、言说、超越/陈鹏
诗版图
内蒙古兴安盟诗人小辑
包立群/樵夫/刘琳/月下成诗/谢晓华/高学英/徐艳君
朱连升/好雨/月光/眉子/北琪/丰慧/雨文/潘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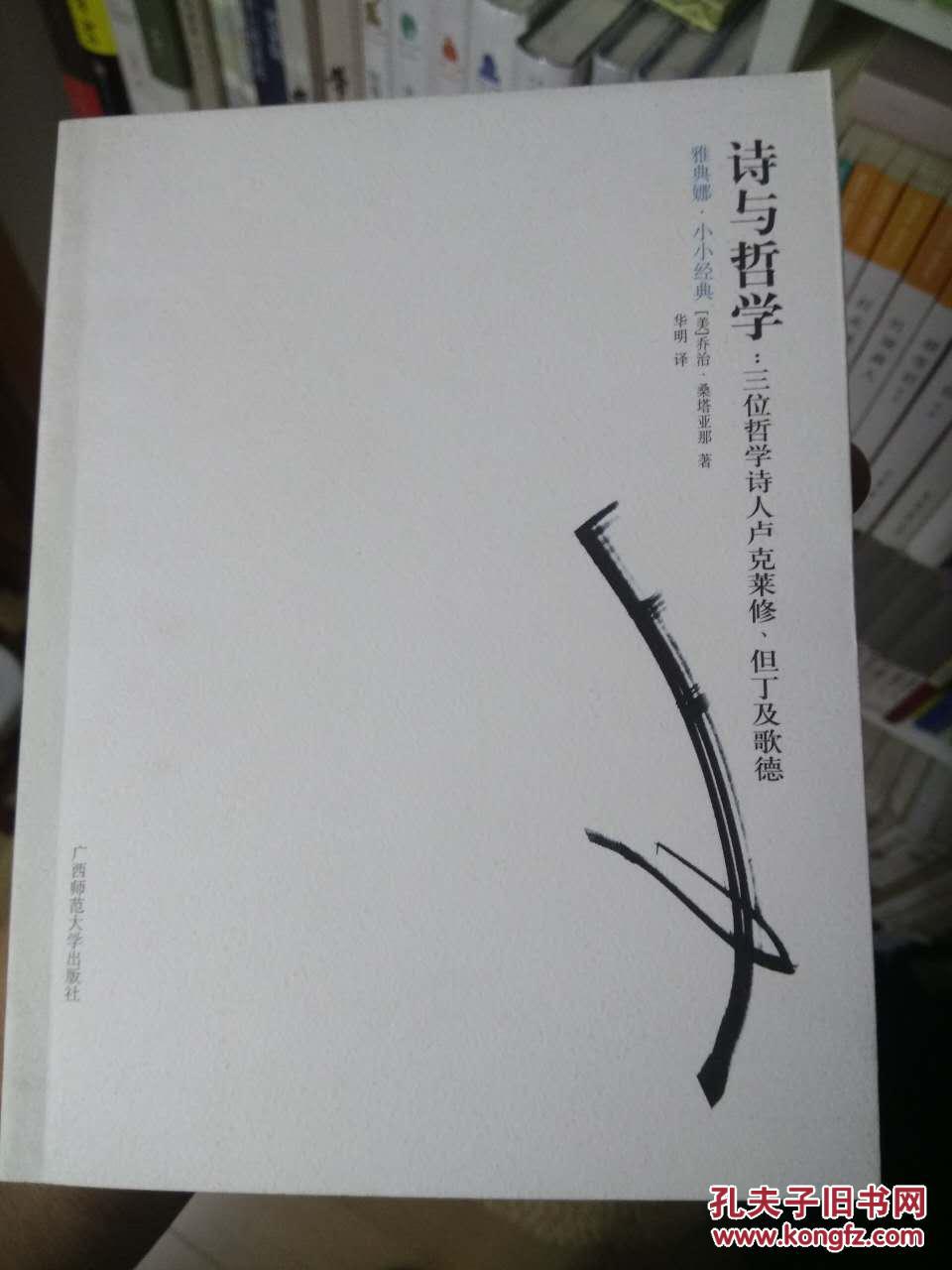
广东廉江市作协作品小辑
龙恒/陈广雄/钟娥/吴强/周树勇/钟海东/支贤
郭怀宽/梁玉娟/许水活
诗人在线
高洪波/皇泯/李德武/卢艳艳/吉小吉/罗广才/水玉兰
高作苦/孟原/鲁西北/刘洁岷/刘纪春/刘伦富/丁瑜
冰洁/黑奔/刘福申/祝凯鸣/俞敏/余风/徐祯霞/无墨
王长征/唐振良/格风/木米
栏目主持人语
头条
先说两个关于小说创作的闲话,小说家麦家语:小说有三种写法,一是用头发写的,叫天才,写出来的作品叫天赋之作,可遇而不可求。一种用心写的,还有一种用大脑写的,经典的作品大多用心或者又用大脑写成的。另一个是,广西作家潘大林说:作家分两种,一种是生活型作家,靠自己生活的底子来写作,一斤的生活只能写三两小说;一种是才气型作家,三两的生活可以写出一斤的小说。
小说与诗歌创作同理,巴音博罗这组诗是用心又用大脑写出来的精品,他俯视东北大地和大地上人们的灵魂世界,在对地理的文化风骨形象的描绘时写出人性和灵魂的诗性影像,他把诸多的生活和苍生的共性及个性遭际,炼冶制成一柄匕首直接抵达你目光之下和喉结之处,让你有窒息感和心碎感。他对笔下的鞍山、大连、辽阳、丹东等东北大地上的城郭的前世今生和这里人们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生存真相,做到了深刻及深邃的揭示、刻画和雕塑,立体的让我们看到白山黑水相伴的东北工业文明下的人们的苍凉、挣扎、奋进和搏击。他是向灵魂深处写作的人,他在为东北大地有生命的万物造像与书写,他把一斤的生活写出了百斤重量的有骨头有血性的诗。
继续说两个闲话:博尔赫斯说,诗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某种东西,诗就埋伏在玫瑰色的街角,随时准备向我们扑来。此外一则是,汪曾祺在1957年7月16日给诗人张明权回信写道:你的诗《更信任人吧》我所以欣赏,应是一种自由,我总觉在生活里所受到的干涉、限制、约束过多,希望得到更多的信任,更多的自由。
恰好诗人李樯在他的创作谈里也说道:诗歌于我来说,就是点上一根烟,蹲守在生活的墙旮旯里,偷窥着众声喧哗中的虚无光影。此外,他也对创作的自由有自己更多精彩见地,他还引用波拉尼奥的话:我相信诗歌带给我们心灵的自由。诚然。他的诗歌“无用”和“好玩”也是我认可的。但我更欣赏他在日常中汲取诗意并把这种诗意荡漾开来,让身边的一切都变得好玩,变得有诗性,让一切庸常和平庸变成有哲理性的优异诗存在。他对日常生活不是一般性的素描,我曾读他的新诗集《挑灯夜行》后写道:诗人的精神内核是叛逆者、批判者和睿智的吟咏者的综合体。他的诗歌其实来自他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诗意的捕捉,他既等诗迎面扑来,更迎风而上去拥抱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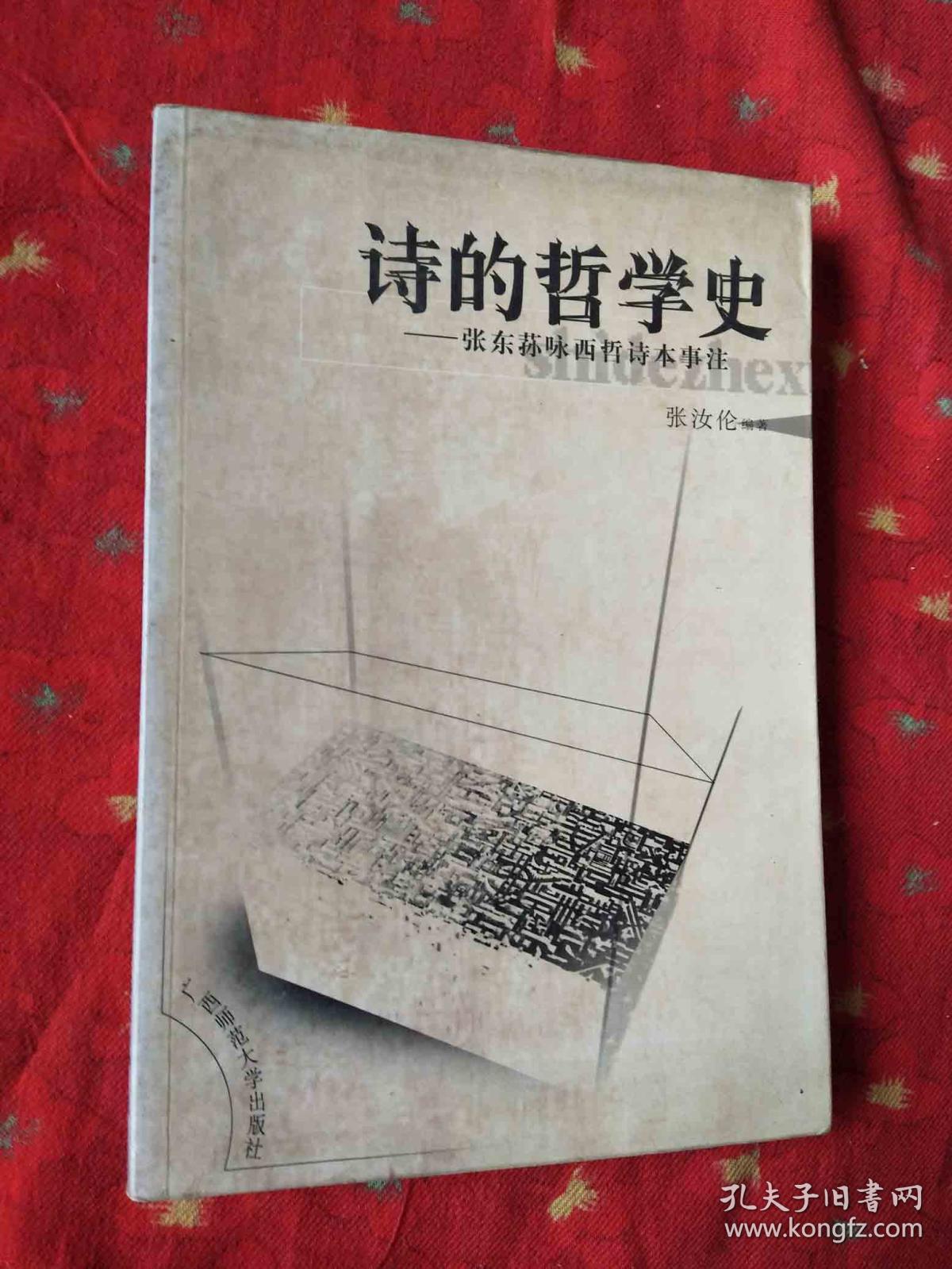
读者可以自观他俩的诗作和诗随笔,文本是王道,我就不再饶舌闲话了。
——李云
投稿邮箱:shigeyuekan@163.com
先锋时刻
宋憩园的诗歌是比较哲学化的。作为憩园的读者,我在几年前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这组诗引起了我的注意。憩园诗歌的哲学化主要体现在“思”上,不是逻辑思辨,而是存在之“思”。面对日常的世界,憩园的笔下却有一种对其“真相”的怀疑。这世界是真实的吗?“周末的早晨,孩子的笑声/将这个虚拟的世界擦亮。”(《诗人的生活》)然而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吗?憩园也许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作为现象的世界,而是更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世界的感觉和意识中。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诗”。“诗就在‘坐’这个字里。”(《哲学》)这几近于玄学的诗句,有着他对“诗”的追寻。他找到的那个叫作“诗”的东西,更像是一种生命的感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憩园对语言的使用。不难发现,他的诗歌在语体上,明显类似西方现代哲学著作,这本身也强化了他的诗歌的哲学化特征。
玉珍的诗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其中深沉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沉重的。我们通常所谓沉重与此有别。因为这种情感与现实、历史并无太大关联,当然,与新诗中的那种“民族寓言”式的情感更没关系。玉珍诗歌中的情感,带有某种焦灼、困境和虚无的特点。它是个人化的,却又是终极的。我注意到,《牛》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况色彩,令人感触颇深。“有一天我明白了人生就是苦难,充满了/生不如死的自我修养”(《牛》)这句诗,似乎可以作为进入她的诗歌世界的钥匙。她看父亲抽烟,然后有了“故事像纸烟一样烧着/像虚烟一样消失”(《抽烟》)的虚无感;在《理想主义》等诗歌中,又有了由“坍塌而解脱”的幻灭感。这些情感,又无不是深沉的,然而又是她独有的。而她在每一首诗的情感展开的过程中,笔法非常细致,层层推进,章法有条不紊,节奏舒缓然而有力。
思不群的诗歌同样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哲学化特征。但他诗歌的用功方向,主要是落实在了语言实验上,在词语、事物和感觉之间,往往产生错位,让人分不清真实世界和现象世界。比如《山塘之夜》这首诗歌就非常典型,他在写作“山塘之夜”这个事物/对象的时候,“山塘之夜”和夜灯下的咖啡桌前的谈话,已经像电影镜头中的溶镜一样莫辨彼此。这种效果是神奇的、陌生的。神奇是日常生活的庸常本身在词语中产生了神奇,陌生是来自揭示了世界在现象背后的“本来面目”而让人感到陌生。当然,这神奇和陌生,直接由诗歌的修辞带来。思不群在诗歌语言的修辞方面有着很高的技艺。另外,从某个角度而言,他的诗歌与憩园的诗歌可能是同源的,都可见到某种现代哲学对两者的共同影响,但是,他们在诗歌表现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李商雨
投稿信箱:lisychengdu@163.com
新青年
李舒扬比较讲究诗歌的气息与气韵的贯通,编者认为诗歌的气息是指诗人日常个性的具体体现,包含性格气质、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比如李舒扬在《童年拼贴史》《春天到了我太开心了》《鱼玄机致李清照》等诗歌中,我们读到“春天的奶奶/也像我的奶奶,用红花绿叶给它织围巾吗?”“春天,你这个没良心的/想了你这么久,你终于发春了。”“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最好,这样/荡秋千的时候,不会见到你”。诗人这种天真、嗔怒和发嗲的语态是诗人气息先于诗歌审美层面的展现,也就是说率真的情愫在没有入诗之前就已存在。而让编者感到惊异的是,李舒扬很完美地将个人的气息与诗歌审美意义上的气韵相融合,气韵是诗歌写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在作品中的特有习性,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神韵峻举,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人如何学会“善的”“美的”“精巧的”等等,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词是被教会的而且是赞同的一种表现,那么年轻的李舒扬用“被教会”的词来保持诗歌上气息与气韵有效的渗透和整合,这自然就生成了诗人鲜明而独立的个性特征。
编者跟踪阅读了95后诗人吴雨伦不少作品,口语化是吴雨伦诗歌的最大特征。新诗百年以来,关于口语诗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减少过,编者倒是认为你可以在诗歌里写“余赠汝一束馨香之玫瑰”,他也可以写“我送你一束玫瑰”,从某些诗歌层面上说两者表达意思一致,没有什么高下之别。编者认为“真”是口语诗歌的第一要义,真实的情感、真正的语言和真切的表达是口语诗歌的三大有机体,缺一不可。本期编者推介了吴雨伦写在美国学习、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的一组诗,见、闻、思、悟,亦可以不见、不闻、不思、不悟或者光见不悟、只闻不思等,这从入诗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大的写作难题,我们欣慰地看到吴雨伦以口语的方式鲜明地呈现如何驾驭与化解大题材的写作能力。
年轻的许氶和刘兰在诗歌的结构、谋篇和技法上有某些相同之处,譬如许氶在《虚构的围救之说》一诗中“或有三万吨鱼骨化成废墟”与刘兰在《它的声音》一诗中的“星星变成碎片,纸片一样乱飞”在比喻层面上说有类似性,句式的布局、语言的跳跃、意象的更替以及修辞手段的运用,两者之间表面看来有不少貌似接近之处,然细加对比,两人还是存在诗歌呈现上的差异性,许氶注重于对诗歌场景和事物的描述,描述过程中故意加大语速的转换,诗歌具有很强的情绪感染力;刘兰侧重于对诗歌场景和事物的抒情,主观成分浓烈,诗歌展现出情感的直流与直露。
——樊子

投稿信箱:fanzi1967@163.com
现代诗经
黄芳的诗具有现代呈现叙事的特征诗歌月刊,她的诗通过视角转换,对生活经验进行选择和提纯,演绎出缤纷而崭新的旧场景。只是她投入其中的情感是新鲜的,并且是有颜色的。比如,在这组诗中所描述的那只泛着“绿锈”的邮筒,“一蹦三跳”的小红靴,一只“不叫”的黑乌鸦等等。当然,她诗中所描绘的颜色也决定了她诗歌的情感基调(反过来也依然成立)。她诗的情感底色是内心充溢的爱,而爱作为一股能量的推动力,给予她情感海洋的荡漾,有时候这激情涌动的速度超过了她内心的承载,因此,她的诗中一直有着淡淡的忧伤萦绕不去。但是,她语言的叙述和表达,又不时透露出达观、笃信和暖意,她毫不掩饰的率真自然给读者带来情感的浸润。
“雨水里也有松动的江山/可以放下忧虑/放下固执的旧我”(《雨水》),阿雅的诗有一种寂静中的喧响,不乏对山水自然的描摹,更有一种与周遭世界的身心交融。“多么好,流水在那一刻有倾世之怀/那一刻,我有赴死之心”(《想一个人去旅行》),语言平静而睿智,有着诗歌情感的控制,诗句中有着向死而生的豁达,自我找到一个表达与释放的缺口。她的诗中有着内心世界的寂静,通过途中遇见,光的照临,投射出那些拥有共鸣的事物,在同期的思考中,呈现不一般的情思——空山的孤独,开花的石头,去体会自然界的无声之音,无形之相,找到一种相互认证和发现。
闫今的诗歌有着她这个写作年龄段诗人所少有的整饬和控制,内敛和自律。她近期的诗歌在形式上都很齐整,每首六行的长短诗句,具有鲜明的气韵和节奏感,具有辨识度诗歌月刊,可以见出她在努力对自己汹涌的诗情予以赋形。她跳脱式的词语表达,善于组织繁密的意象,消除时空的限制,将碎片化的现代生活裸裎无疑。她对意象叠加的诗歌语言形式的追求,对诗歌画面感场景的迷恋,让她尝试以意象作跳板,在不同的意象元素中对诗歌进行横向扩张。对于年轻的诗人闫今,感性和生命力是如此充沛,使得她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进入一种感性化的个人写作,去发掘、去体验,去重新定义周遭世界。
——微蓝
投稿信箱:lingjun03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