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的词坛创作,处于由前期的壮志转向回归风格的平民化时期,由所谓的“江湖名士”傲啸词坛,再续文翰。由于词体功能的分化和深沿,平民化时期词风的发展分为两端:继承和发展于辛词的“稼轩风”,抒情慷慨,豪情旷怀;或者再传于周邦彦、姜白石,重于诗词格律之偕,字句工琢,不尚抒情与任性。其中状写恋情景物,山川林泉的避世之作,成为南宋后期词体的主要风格。戴复古、孙惟信、刘克庄、陈人杰等担负起此阶段的主要创作,表现出对于自然隐逸风致的寻求和遁世之志。由山林文士撰填的游景词、咏物词与少数规复词的悲壮之风,构成了宋末平民词的主要体例与布局。
一、南宋后期平民词体缘起,是由于宋代以后词体创作的外在环境气局的弱化与平民词派作者自身的审美观

念与词风的转移,使平民词体产生了主客观创作因素的加强。其中,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真婉约词风的形成,导致了宋末词风格局的普遍弱化与清雅化的出现。其后由于“开禧北伐”失败,宋军丧师失地溃退千里,作为主战派人物的韩�胄被传首北廷,南宋上下之儒臣与文士俱知事已不可为,局已不可挽,导致了南宋后期的词体风格的低沉与颓化气象的形成,所组成的主要词人群体已经由辛派词人的朝政之群转为江湖山野的文士,创作的心态也由壮志激烈的恢复之声转化为知其不可而避之的伤婉之音。

二、宋末壮词主要作者创作群体的平民化,是平民词创作代替宫体雅词的重要标志。宋末宦场的腐朽与淆乱导致了朝中文人的醉生梦死与放弃时政。与此同时,作为心有不甘的壮志恢复的文士,在颓败的时局中犹自发出意气消沮与不屈之音,体现于词中,即呈现出稼轩之激昂而悲凉的词体风格。例如黄机《六州歌头》、王涯《满江红》等,俱是以伤痛低沉的情感唱出志图规复的悲壮之音。这是沦落与徘徊与山林的下层文士的自觉呼喊与报国志节的体现与闪耀。究山林文人形成的原因,率皆由于宋代制度之官冗政繁,弊生国困,科举屡开而进者不得其用。故而山林文人所作平民词,每每怀骚而负气,清雅而疏宕刚劲,盖其气未伸而远拓。故“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而清刚,变驰骤而为疏荡”(周密:《宋四家词论目录序论》)。刘熙载亦云:“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艺概・词曲概》)。这样的词体思想来源导致了平民词中壮词与清健词的“骤然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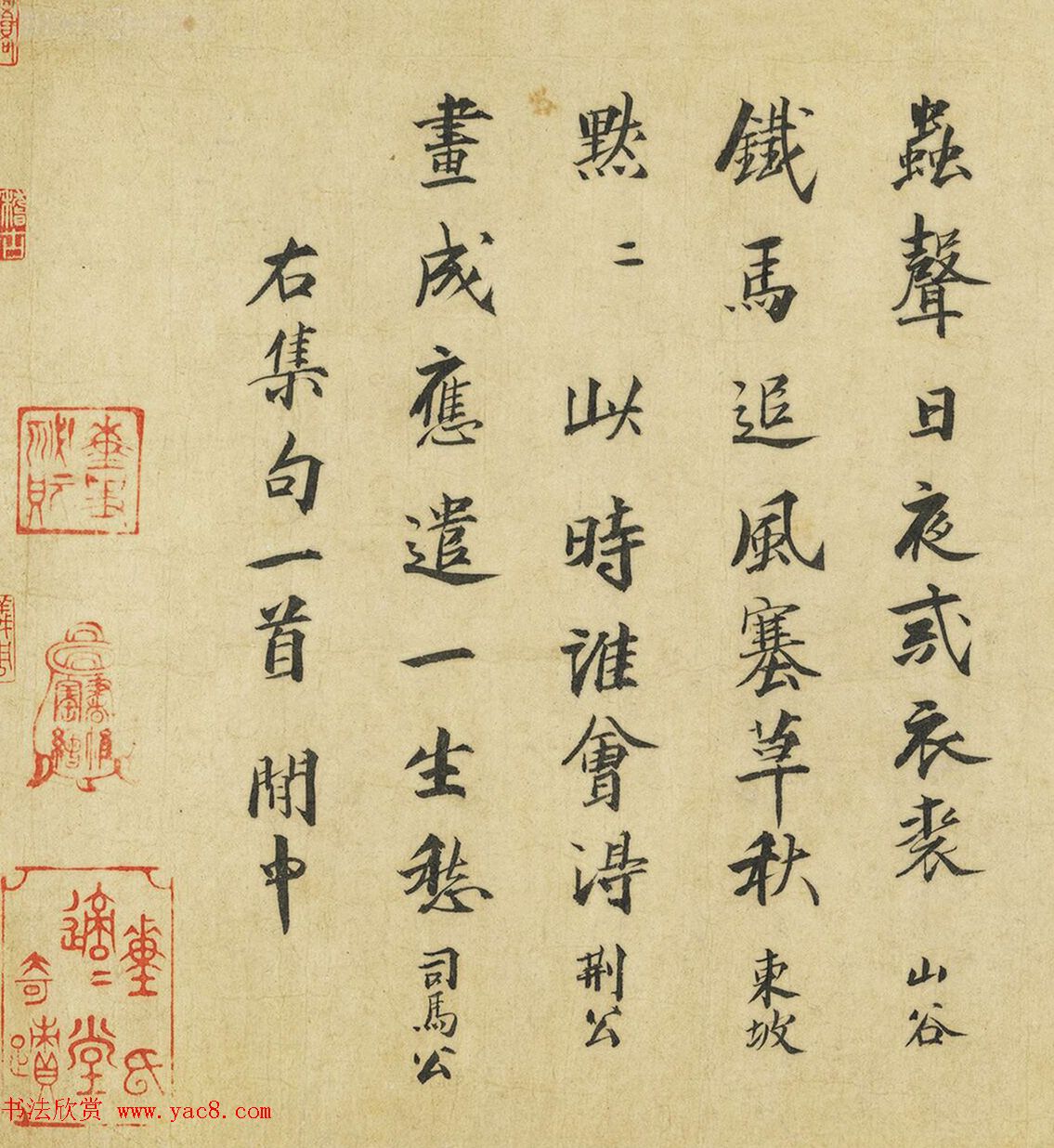
三、南宋后期平民词体对雅化的提倡,表现出宋末词体发展的成熟与格局的协律化倾向。平民词与雅体词于此更无太大的区别,协音律、崇雅正、主深致、尚柔婉既是其词中“韵”之内涵,亦为其所追求的词体艺术之审美理想。辛陆词体的气节与疏拓不羁的风格已经难觅踪迹,渐趋婉转与工丽的词风强调与辞藻之典雅与音律章法的精审协调。由先之“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闲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张炎:《词源》)转而成“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为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体现出宋词体例的成熟与格局气象的衰落,两种过程并行于宋末平民词的创作过程中,体现出季世倾末的文风与词创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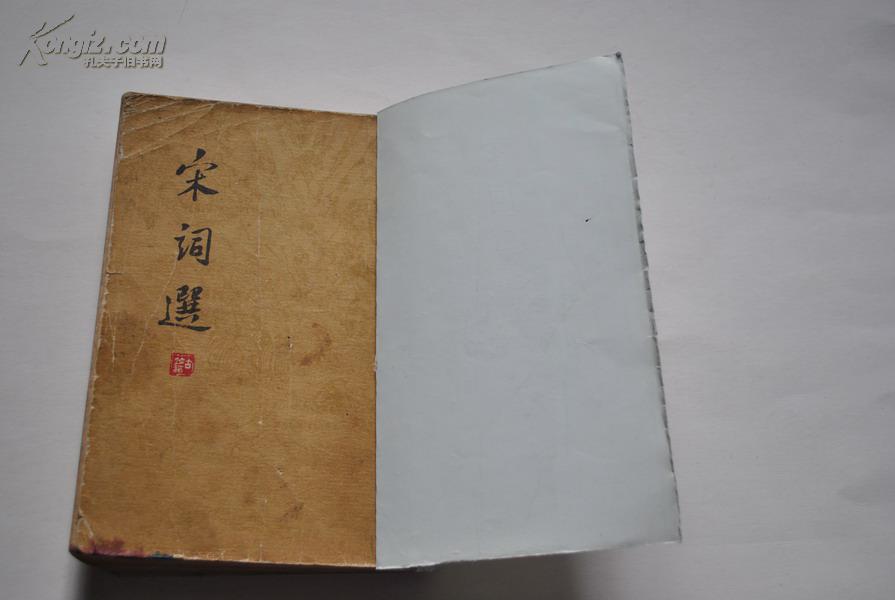
四、白石体的再传与流变,结社与咏物使平民词的创作泛化,并臻至创作的高峰期。宋末文人关于姜夔词作的推崇与效仿使平民词体趋与精工与成熟泛化的历程。南宋后期平民词人承接于白石词风,得其清逸而失之刚劲,对于家国之悲、偏安之耻未尝以之为意南宋后期诗词,而是沉浸于词体的柔化取嫣、游乐、应酬、消遣的悲观寄托之中。同时,外在的清客养士之风,使平民词的发展得到滋生的环境和意识导向。其时以文词牟利,受赏识而获利的记述往往皆是,例如翁孟寅宾曾经“�游淮阳,时贾师宪(师道)开帷阃,甚前席之。其归又置酒以饯,宾�即席赋《摸鱼儿》。师宪大喜,举席间饮器凡数十万,悉以赠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同时,布衣之交的平民诗人结社和唱酬风习的形成,使平民词作的创作面与词人群体扩展至于结社与酬唱的性质南宋后期诗词,起到相互促进与评点的作用。再次,咏物词的工细与广泛应制,其风“潜气内转”,以辛词豪壮的自我抒情词婉化和细化,开创表现感伤情怀的纤巧精细词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