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学员,大家下午好:
今天讲的主题是昌耀先生,我在其他地方讲过昌耀先生的诗歌,唯独没有在青海讲过。在昌耀先生的诗歌里面涉及到青海的很多意象和物象的密码,所以咱们青海人应该对昌耀更有感觉,讲起来可能会更有意思。
说到昌耀诗歌的语言艺术及精神高度。主要有两点。
第一、对昌耀本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
第二、介绍昌耀的语言艺术方面的特征。
昌耀先生简述
1988年,《十月》杂志的编辑、诗人骆一禾与他的夫人张扶博士为昌耀先生写过一篇评论。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诗人不是自封的,评价要由别人来说,因此,我们尤其感到必须说出长久以来关注昌耀诗歌世界而形成的结论:昌耀先生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
1988年8月,《西藏文学》举办了一次“太阳城诗会”,我和昌耀先生都参加了,北大的谢冕教授肯定了骆一禾对昌耀先生的评价,说:“同意昌耀是大诗人的说法”。骆一禾是北大文学系的学生,也是谢冕的学生。谢冕教授是中国诗歌批评界的最高权威。
1998年,《人民文学》的主编、诗人韩作荣为《昌耀的诗》做了序,他称“昌耀是诗人中的诗人”。这也是一句最流行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说法。进而指出:“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价昌耀,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作相比,也不逊色。他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
“诗人中的诗人”,有两个意思,一是可以理解为是诗人中最好的那类诗人,不是说最好的诗人,而是最好的那一类诗人。另一个说法,就是当年的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的时候说他是“诗人的诗人”,这个表达缺一个“中”字,但是意思不一样,诗人的诗人,这种诗人是能给其他诗人以启动能量的那种诗人。我们认为一些好的诗人,能读懂和欣赏他的诗歌的人,也是少数。比如很多人都知道汪国真,汪国真的诗歌当年很流行,读者面很广,但汪国真在诗歌界不进入评论的范畴,认为他很浅显,没有什么可评论的。诗人的读者也分多少,但是读者少的诗人,也可能意味着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需要相应的能力来读他的诗,他不仅是诗人,还给读者写诗,能让其他的诗人受到启发,能获得能量。
2015年《新型诗刊》的主编巩学敏,在昌耀先生去世15周年时,在微信里发了一句话“昌耀是当代诗人中最好的,没有之一”。
2010年我在威海和当时《诗刊》的编辑雷霆,他问我知道昌耀吗?我说知道,他说昌耀这个人很特别,中国只有他一个人那么写诗,他跟谁都不一样,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昌耀先生有他的独特性,没有人能学到他,或者这种类型的就他一个人能写诗。所以说昌耀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诗人。
我们评价一个诗人,我们说不出更好的赞美词了,就说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真正独一无二的诗人几乎没有,所有的诗人都有一个类型。而昌耀一个人就代表了一种类型。
下来我们对昌耀和其他类型的诗人做一个比较。
1936年昌耀先生出生语言的艺术 诗歌, 1950年代往后的中国诗坛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任务,比如公刘、李瑛、白桦、绍燕祥、蔡其矫、曾卓、牛汉,这是1950到80年代最重要的诗人。
公刘在50年代写过诗歌名篇,叫《五月一日的夜晚》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
空中朵朵云烟,地上人海灯山,
数不尽的衣衫发辫,
被歌声吹的团团旋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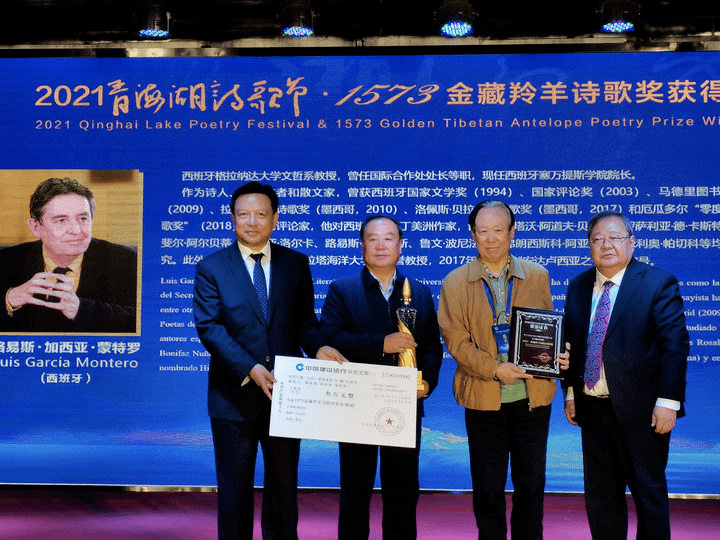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
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
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这是很著名的诗句。把这个诗放在现在看,也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50年代延续到现在,这种诗歌是主流诗歌的一个特征。这种主流诗歌的特征有三个特征:豪迈的主体基调、实地歌手的立场、社会学的主题。
70年代末的朦胧诗兴起了,它的基调完全跟前面的豪迈、时代歌手完全相反,他从歌颂反转为置疑,对时代的置疑,过去岁月所经历事情的置疑,从原来歌颂的立场转变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这也代表了诗人们自我思想的崛起。比如北岛有著名的诗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还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就是他从在文革时代过来以后产生的感受,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揭示。
1962年的时候,昌耀先生所写的《峨日朵雪峰之侧》,(注:峨日朵在祁连山境内)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地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
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
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
呵,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在锈蚀的岩壁;
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
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
读了公刘的诗,再看昌耀先生的诗,他写的是大自然、岁月、生命、是在深山秘境中的大自然之中感受着大自然的力量。所以,人在陷入岁月的困境中,通过顽强的自我搏斗,生命在岁月中的磨砺和复杂的精神生成的磨砺才是诗歌所要探讨的永恒的主题。
与此同时,昌耀先生在诗歌中应用的是中国汉语诗歌中一种完全由他独创的、陌生的、孤决的、矿石般的语言系统,是在其他诗人的诗歌里没有出现过的,这也是他的诗歌最为让人激动魅力所在。我当年读昌耀的诗歌,首先惊奇于这套语言,因为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语言,一个诗人,他能创造出这么一套语言来,让你觉得很神奇,里面充满着张力。所以,这就是昌耀先生的诗歌最让人激动的魅力所在,也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昌耀先生的诗歌和他一生一样,都处于一种自我搏斗的艰难的攀爬中。要了解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则需要从他的人生中寻找答案。
1936年昌耀先生出生在湖南桃源的一个大家族,他家的房屋几乎占了整个村庄的一大半。14岁在县城上学的时候,瞒着家人自作主张报名参军,成了38军的文艺兵(38军是朝鲜战场上特别能打仗的一支军队)。昌耀先生参军以后,不久随部队进入朝鲜战场。
1953年夏季,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负伤了,同年秋季回到国内进入河北省荣军学校。昌耀先生在朝鲜战场的时候就开始了写作,当时还有一批写作的人,比如说湖南著名的诗人未央,入伍前在很多地方发表作品,可能由于这些人的带动,他也开始了写作。他们大量的往国内投稿,昌耀先生的第一篇作品在上海的一个文化学习的杂志上面发表了,发表时候他只有17岁,虽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能力,但是能说明他是一个在文学上很痴迷的、很有热情的一个人。此后昌耀先生在河北荣军学校读了大量的书,发表了不少的作品。
1955年6月学校毕业季,青海省到河北荣军学校去招聘,号召大家支援大西北,昌耀先生就自作主张报名参加,来青海省贸易公司当秘书。
1956年青海文联组建,文联负责人广纳贤才,就把昌耀先生调到文联。一年之后,因为两首诗,别人分析他的诗有问题,就被打成右派,昌耀先生到了湟源县的日月乡,在干活的时候,受到生产队长的各种刁难,百般忍耐之下,昌耀先生忍无可忍,和生产队长大吵一架,生产队长报到公社了,当天晚上县上的公安局就把他带到县公安局的拘留所拘留起来了。昌耀先生又开始了进一步的劳动教育,在湟源县哈拉库图乡大炼钢铁,之后在西宁的南川的新生铸管厂炼钢。
昌耀先生开始了他的流放岁月,先是到了祁连山八宝农场待了十多年,后来又转到海南的新哲农场。
1979年,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甄别右派平反,昌耀先生又回到青海省文联工作,这个时候他已经历经21年的流放,昌耀先生43岁了。
1979年的10月,昌耀第一次在全国顶级刊物上亮相,发了一首《致友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九死一生黄泉路,
我又来了
骨瘦如柴
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
昌耀先生当年不服,现在好象更不服了。虽然骨瘦如柴,但是不服的劲头憋的更足,正是这种不服,成了昌耀先生写作的动力,他胸中急需的火山要寻找一个出口、写诗就是他的出口。
1980年第一期的《诗刊》上500多行长诗叫《大山的囚徒》,这是他对自己形象的代表,我是大山的囚徒,这是他对自己的称呼。接着又是《山旅》、《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构成了他自传性的“流放四部曲”。从祁连山一个人的流放,到奔向红星高挂的北京去告状,这四部长诗对流放生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书写。
“流放四部曲”在我看来是中国一代落难知识分子精神史诗式的作品,其中对于生命在大苦难中的不屈不挠、高原秘境中酷烈壮美的大自然、古艳浓郁的藏族民俗风土、都是昌耀诗歌里最重要的东西。
“慈航”是宗教的名词。就是慈航普渡,《慈航》这首诗表达的是一个是在藏族人民之中获得了爱、结了婚、然后想用一种宗教的救赎来表达,所以叫慈航。《慈航》是当代新诗史上的一个绝品,没有人能再写出这样的诗歌。
1979年到1985年,是昌耀先生生命状态最强盛的时期,相继写出了关于青藏高原的造型的一系列诗作,有《旷原之野》、《河床》、《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巨灵》、《牛王》等等,《河床》这些诗当年有很多人朗诵过,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
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
目送我走向远方
这几句诗歌表现了在青藏高原上,那种神奇、孤独,大男人独自而行的一种状态。

1985年,昌耀先生的诗歌中一味的发出了叹嘘,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
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我认为这显示了昌耀先生的精神状态从强盛的巅峰开始下滑的一个信号。让他这么叹息的除了家庭关系,还有事业上的不顺心。这时候昌耀先生已经49岁了,生命的激情有点衰退。突然觉得自己的日子跌入了一地鸡毛的平庸之中,进而体会到一种深刻的无聊、疲倦和荒诞感。
这个时候,昌耀先生对奋斗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诗歌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其中我举几个例子:
行者的肉体已在内省中干枯颓败耗燃
还是不曾顿悟。
人生有不解的苦闷
无话可说
激情先于本体早死。
生活总是一场败局已定的博弈。
我看来,他的这种感受正是一位大诗人的生命的一种预警机制和加力机制的启动。为了从这种困境中自拔,他先写了好多古代的艺术物象。
接着昌耀先生骑着自行车重走了当年的故地——湟源,在这个时候,他又创作了一大批诗歌,有《远离都市》、《故居》、《极地民居》、《在古原骑车旅行》、《听候召唤:赶路》。
可以说,昌耀先生所有重量级的作品,都是在陷入困境的自我精神搏杀中产生的,这个期间,他写出了他另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这是可以跟《慈航》来并肩的一部作品,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本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是和《百年孤独》很相像的一首诗,大概有三几百行,也是一部里面浮藏着大量信息密码,让我自己爱透了的一部作品,就是《哈拉库图》。
首先是这历史上的汉藏边贸之城,在日月山附近,可惜现在只有遗迹了,当年是汉藏交界的分水岭,西边是藏族地盘,东边是汉族的地盘,友好的时候在这里通商,很繁荣。底下有一个村庄,因为卡哈拉库图而得名,昌耀在流放期间在这里炼过钢铁。这属于昌耀先生重返故地走的比较远的一次。
30年后重访故地,遥想当年哈拉库图城的繁荣和村庄的兴旺,现在看到的是一片的衰败,就像咱们现在看到的空心村一样。现在看来,村里有的人是他认识的一些人,当年知道的一些人,死的已死,老的已老,一片破败,他自己心里非常沮丧,这个时候更加感受到生命的徒劳与虚无。
就是在这种徒劳和虚无感的沮丧中,他被村里的一个人上了一课。这个是智商有问题的一个人,他吹着唢呐,在村里引来一帮村民,给人用说唱的方式讲故事,这人也没有其他的生存能力,但是日子还能过,还能吃上饭,他是精神享受,他需要召集一帮人听他在那儿讲述一个故事,他每次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是一个有关“憨墩墩”的故事,(“憨墩墩”是对小伙子憨厚、结实,还有点倔的人的一种爱称”。他显然是村里人调笑的对象。但他自己则把一天说唱当成了自己不朽的大事业,村民不怀好意的逗他,你整天唱的“憨墩墩”什么?有本事了你说一说,“憨墩墩”的相好,为什么把他叫做憨墩墩呢?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很狡猾,一脸的高深莫测的样子,为什么叫憨墩墩?他说:“憨墩墩嘛,至于憨墩墩嘛,那意思深着…憨墩墩,那意思深着…深着…深着”。
中国的民间的百姓有一种高于一切的喜乐精神,我们在生存里面要找到一切东西来寻找开心,这是昌耀先生在“憨墩墩”村民身发现的一个生命伟大的秘密,正是这样的生命机制,让这些村民忘生活中无尽的苦难,只要一天有心就好。
这是《哈拉库图》里一段憨墩墩引述。我当年看的时候特别的兴奋,我觉得昌耀一生给人的感觉是抑郁拘禁,但他本质上保持着一个需要藏的很深的坏孩子式的天真和玩劣,包括写作,当他憋不住的时候偶尔玩劣一把,总能传出放电般的精神奇趣,我觉得太微妙了。关于关于“憨墩墩”的这段话,惟妙惟肖的模仿,既让人大乐,暗自叫绝,更加让百姓复杂的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

正是哈拉库图人的大智慧,那种喜乐精神,调整了昌耀的人生姿态,他原来感到苦闷、颓废。但他看见人家活的那么开心的,我为什么不能?他原来的苦闷焦虑也被哈拉库图的智慧调整到松驰、淡然了起来。
1990年写的,昌耀先生有一首诗,《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便帽就是鸭舌帽),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的造访,当戴着便帽从城市到城市走访的时候,已经不苦闷了,拿哈拉库图人调整的他也会玩了。另外一个他这个时候获得了一些机会,相继以著名诗人的身份前往上海、杭州一些城市参加诗歌活动,或者担任诗歌赛事的评委,在这些活动里,他感觉到非常愉快,跟很多熟悉他的作品,多年没见过面的人,或者是另外一些早就想见面,没见过的人聚一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是这种逍遥的姿态没有保持多久,接着是国家的宏观背景上,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时的情况是人人争先下海,各显神通,整个社会进入了以财富为王的商品主义时代,昌耀先生又面临新的人生变故。
第一个变故,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破裂了,离婚了,离婚以后,在身体、心灵双重归属感的渴望中,他的人生发生了两场恋情,第一个恋情的女主人就是上次上杭州评奖担任评委获奖的一个女诗人语言的艺术 诗歌,这个女诗人我当然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昌耀用的是英语字母来代替,SY,就是傻丫,给她起了一个昵称,可见是很用心的。另一位是西宁本地的,在一个机关工作,也是单身。
显然这两个事情最后都没有完美的结果,昌耀为这两个先后写了一系列的诗歌,在他的诗集里,线条很清晰,这是写给谁的,那是写给谁的,基本没有交叉。两场恋情都是开始的时候不无暖意,到了最后把他放到火上,他用了一个词叫烘烤,放在火上烘烤的感觉,最后让他在一种被金钱打败的感觉中心灵流血不止。比如说傻丫要出诗集,那时候诗集进入商品主义时代,都是自己掏钱出,谁出诗集会让周围的人非常羡慕,但是傻丫在出诗集的时候,昌耀先生觉得他的经济能力不行,给傻丫寄了100块钱,说希望能给你起点作用。傻丫很快把100块钱原路返回了,昌耀接到100块钱以后非常的羞辱,觉得受了致命一击的感觉。
另一位女性,他们的关系一直进展不顺,俩人别别扭扭,经常斗嘴。她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的,是一个有钱人,要给我买一个豪华游艇,要带我去世界上周游,这显然是吹牛,但昌耀当成真的了。后来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有钱人,昌耀先生觉得我失去了她是被金钱打败了。昌耀先生开始对金钱主宰的时代开始变的非常的痛恨。
第二件事情,随着家庭的破裂,他把房子留给了前妻留下,自己带着铺盖卷,开始先住在省作协一个大办公室的椅子上,晚上拿铺盖卷睡,白天放在报纸上,晚上再拉开,他自己还在那儿做饭。后来摄影协会隔开半间房子给他,他成了那个办公室的一个寄居者。他开始非常无聊,经常一个人在大街上晃,俨然成了一个“大街看守”。
昌耀先生少小离家出走,流放中无家可归,到了54岁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无处置放身心,也失去了心灵的寄托。这就是他的命运。
这个时候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他是个诗人,他这个时候写了一种诗歌,不分行,就像散文诗一样,一直这么转下去,不分行,这本来叫散文诗,鲁迅的《野草》就是那么一种体式,但是昌耀先生却不,说我就是诗歌,不爱叫成散文诗,我这是就是不分行的诗歌。他用这种文体表现了一个当代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带有无家共性的底层人物系列。
1998年,这位大街看守立地成佛般的摇身一变,以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身份出访俄罗斯,并写下了他晚期最为博大,最具有华彩风格的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曾有一代苏俄诗人点燃了昌耀先生对社会理想的国度向往,但他现在看到社会重新分化为穷人和富人两个世界,这正是昌耀的心头之痛,金钱主宰人的情感,主宰人的生活,主宰人的选择,他从两次婚恋有了深刻的感受,对金钱的问题特别敏感。
他在这个诗里面,又铺展开了他对另外一个大时空中的俄罗斯的描述,他熟悉俄罗斯,熟悉那些辽阔大地上粗重辉煌的历史和磨难,熟悉文学史上那一长串响亮的名字,引导了他人生理想的勃洛克,博大悲悯的老托尔斯泰,与他同样经历了流放和人生屈辱的佗思托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们。他从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里获得了非常多的东西。昌耀诗歌里对土地、大地的表达,对俄罗斯诗人,对俄罗斯广袤大地气质的表达是相通的。他熟悉这一切,也熟悉那一长串的名字。这应该是昌耀整个人生中最为酣畅放纵的时刻,他无所不知的承接着交谈中来自任何一个角度的话题,在诗人的国际主义圆桌上高谈阔论,纵横捭阖,参人类忧患之心,持诗人天纵之才,他表达了一个生命历经无数重的地狱之难,最终要抵达天堂模式。他在诗里接下来写到:
看啊
这是太阳向着南回归线继续移动的深秋,
在月明的夜空
天际高大幽兰,
从波罗的海芬兰湾涌起的白色云团
张扬而上
铺天盖地
好似升起的无穹宫
而东正教堂的晨钟
已在纯金镶饰的圆形塔顶清脆地震荡。
两年之后,当他在病痛折磨中,朝着病房的窗外纵深一跳,这位殉道者的一生至此已彻底完成了。
昌耀的语言艺术方面的特征
我们都知道,文学艺术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前面也提到了昌耀先生诗歌语言,虽然没有着重的介绍,但是我们也能感受他跟其他同时代的诗人完全不一样的语言魅力。
语言到底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一部作品首先进入你的视野,并决定你是否要把它读下去,就是它的语言。我自己是一个搞诗歌评论的,一天寄到我那儿个人的诗集、诗歌刊物、文学刊物非常多,有些是一些熟人的,我当然要看,但是一般的我都没法看完,要不熟悉的人,我会翻开,拆开要看一下,就是看上一两首,你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诗,决定我读还是不读下去,它就重要到这样的地步。
为什么语言能有这样一种能量呢?高质量的语言是一个诗人艺术天赋、精神强度、美学理想跟文化积存的综合体,语言代表这么多的东西,你的美学理想,你的精神强度,还有你的文化积存,文化积存主要是你看了多少其他的东西,从那儿能转过来,转化成你的语言,诸有此类,它是一个总量,语言代表着这个混合体,语言绝对不是思想的载体,同时是一个可以欣赏的独立体。所以,语言是带有能量的。
我去年在诗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比如有些语言,像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没人这么干,她这么干了,用这样的构思方式把句子串起来,是一个非凡的人才敢这么干,才有能力这么干,这几个叠词一下能传达精神上的状态,把孤独,惶惑,凄惨的心情一下子传递出来了,所以它是有能量的,高质量的语言是有能量的。
如同一个高密度的压缩芯片,其中浮藏着万千气象,芯片的密度小,其中的含量就小,平庸的语言没有密度,不构成一个芯片,因为一览无余,这就是语言,我自己感觉的几个层次。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曾经熟记过,50、60年代以来,诗人笔下写青海草原的诗歌,当时从50、60年代写诗歌的模式,几乎都是用田园牧歌式的套路,白云、蓝天,镜子似的湖泊,滚动的羊群和牧羊女,完全是一种美文的画面,都是这样的东西。
当然,再往柴达木,那边石油工人,地质勘探者,乐观主义精神之类的,就是这样的表达,80年代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个事情,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作协诗人,上柴达木去写西部,他们先到柴达木回来以后到了西宁,青海作协把这一帮人叫到一块,又把青海的业余作者、诗人叫到一块,大家一块交流一下,主要是听听人家谈文学、谈艺术。其中有一个柴达木来的诗人,叫粱尚泉,在当时是影响比较大的诗人,他念了一首诗他认为不错的诗:
巍巍昆仑山,身姿多壮美;
头顶白雪,山腰青翠;
多像咱石油工人,健康又魁伟
身着蓝工装,头戴银铝盔。
这个诗就代表了当年的流行诗风,它简洁、明朗、构思巧妙。我当时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一直记到了现在,如果没有以后的诗歌我们认为这种诗歌是最好的诗歌。
但这样的诗歌却经受不了时间的筛选,我们今天再看这首诗,我们不能说人家是小儿科,但是起码太肤浅,太表层化。这就是当年写青海草原、西藏草原一种套路,就是艺术模式决定了大家都是那样的写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昌耀先生改变了关于青海高原的诗歌写作模式。他曾写过一首《鹿的角枝》。
在雄鹿的颅骨,生有两株
被精血所滋养的小树。
雾光里
这些挺拔的枝状体
明丽而珍重,
遁越于危崖、沼泽,
与猎人相周旋。
若干个世纪以后,
在我的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