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访谈录摘抄
采访者:七小姐
问:据我所知,您经常应邀到中国大陆去参加诗歌会议与讲学,与中国诗歌界有过密切的接触,不知您对当前的中国诗坛有什么看法?
答:从1988年两岸开放以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大陆开会、讲学、访友。我和老诗人如艾青、卞之琳、辛笛,中生代诗人如舒婷、顾城、杨炼,以及年轻的第三代的瞿永明、欧阳江河、王小妮、于坚等都有着深浅不同的交情。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和更年轻E世代的诗人就少有接触,但并不少读他们的作品。时至今日,我不无遗憾地感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E世代诗人群都陷入一种语言贫瘠,缺乏隽永诗趣的境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毫无兴趣,即便对优质的汉语都没有掌控的能力,写的诗句似通非通,更不用说创造意象的能力了。
诗歌的语言应求其自然流畅,精致准确第三代诗歌欧阳江河,所以最佳的诗歌语言应是日常口语(我称为生活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有机性融和。独倡书面语言则过于文雅和做作,强调口语又可能流于口水而变得琐碎庸俗。今天大陆诗坛主张口语和叙事,理论上没有什么不对,但以具体的作品来看,大多朝着“非诗”的方向倾斜,而非诗化首先经由散文化,一首诗的整体结构完全吻合作文的“起承转合”,而句法与分行都遵守严格的逻辑,他们鄙弃意象、拒绝暗喻,他们只会用口语,可是口语毕竟不是诗啊!比如从菜市场买了些青菜萝卜,加点油盐炒一炒,便算是菜肴了,就烹饪艺术而言,这只是处理素材的最初阶段。我一向反对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使作诗如作文”,可谁都知道,诗与文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胡适改革了诗的体制和语言,但不幸同时也革掉了诗。中国许多诗人一心追求大众化,主张诗要写得明白易懂,但那些粗糙的大白话,那些直线写作的叙事手法,懂是懂了,却发现只不过是一篇毫无诗意的文字。其实诗与一切艺术一样,都要有“味道”,既要有外在形式的美学味道,也要有内在涵咏的哲学味道,两者兼有固然最好,但至少语言这第一口菜要咽得下去
所谓的“非诗化”,就是以大白话说出一堆废话,以最多的话语说出最少的含义,主张崇尚低俗,反传统的一切美学质素,走一种“化神奇为腐朽”的偏锋。有些评论家把这种现象归类为“后现代主义”,譬如近年在大陆搞得有声有色的“下半身派”、“垃圾派”。我把这些现象视为一种新型的“原始文化”,他们颠覆传统的道德规范与美学本质,显然已对当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形成一种挑战。我个人并不反对写性,以性入诗,最终它必须是诗的,要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只是使人恶心的性描写。
当然,今日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任何变化都有可能,都难以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文化的多元趋向。也许我的看法比较保守,但合理的创新,有效的写作总是大家一致的期许。
问:有人说:40年代后第三代诗歌欧阳江河,台湾诗歌走在大陆前面,80年代后,大陆诗歌走在台湾前面,不知您对这种说法有何意见?可否请您谈谈大陆诗歌与台湾诗歌的差异性?
答:大陆诗歌与台湾诗歌最大的差异性是诗的观念。大陆诗人重视传达,诗歌的功能在达意,诗人的使命是通过诗歌来体现一种社会责任,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诗更是沦为政治的工具,到今天仍有大部分诗人认为诗歌必须具有某种可以“知解”的现实意义,个人化的抒情或心灵写作是无价值的。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绝对论会不会是另一种偏执?李白、杜甫等的传世不朽之作,不正是那些没有什么社会责任的作品吗?大陆诗人特别重视“写什么”,而忽略了“怎样写”,这一说法虽不是全面现象,却是主流现象。他们只想把“意义”说出来,而把赖以产生艺术感染力的意象、暗喻、抒情等视为并不重要的技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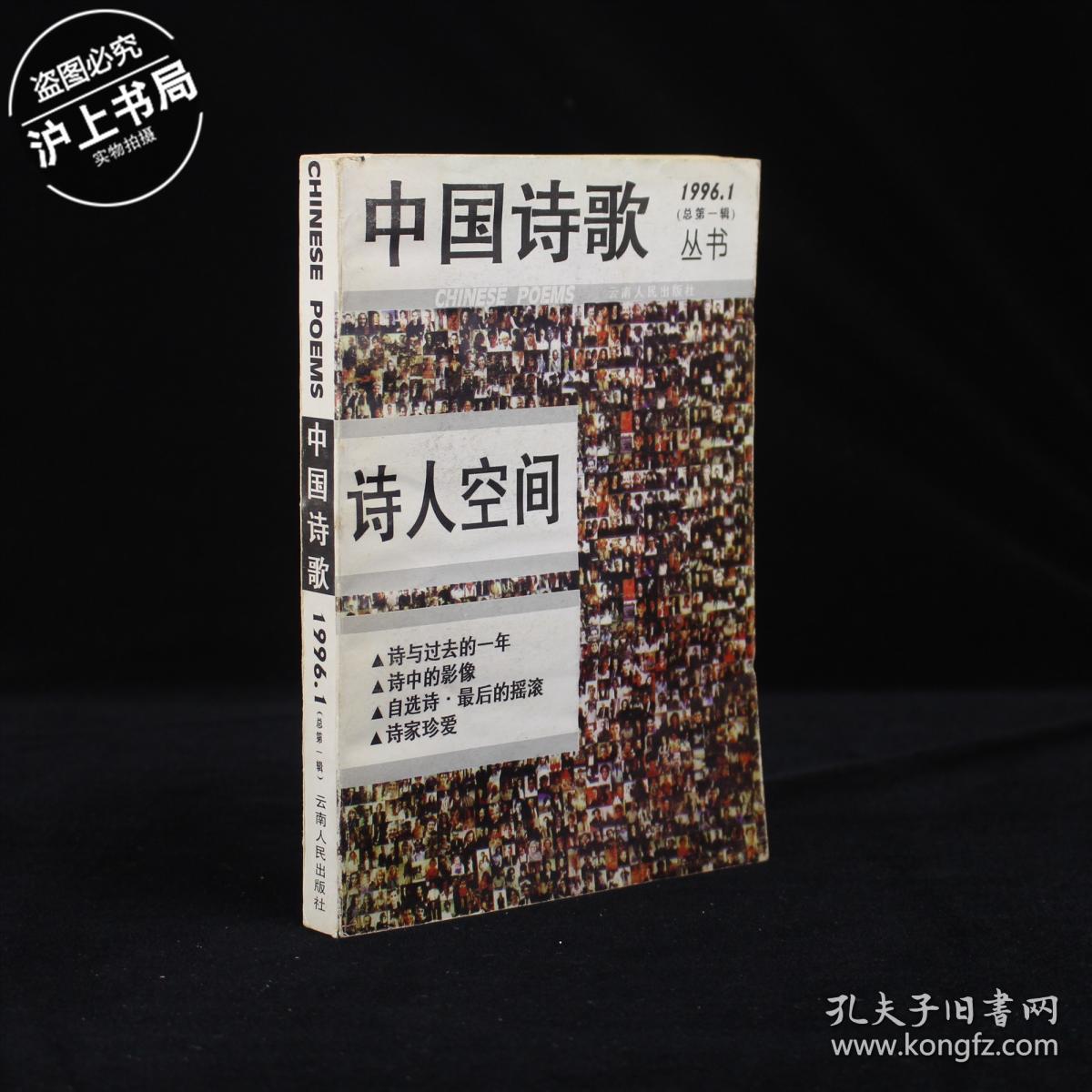
台湾诗人通常认为,担负社会责任是社会学家、社会运动家、政治人物的事,诗人只负责把诗写好。当然,好的诗,仍然与人生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诗人张扬了社会责任而忽略了诗,这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失败的诗人。所以相对而言,台湾诗人侧重“怎样写” ,至于“写什么”,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没有条条框框的社会中,他们什么都写,什么题材都可入诗。在5、60年代,在所谓“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当局对政治思想的管制也是很严格的,但并不影响现代诗的发展,否则我的《石室之死亡》就不可能出版。
台湾诗人早期都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从欧美现代诗歌的经典中挖出了不少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诗不是一种概念的陈述,或意见的表达,而是一个意象世界的呈现。不过当时诗人过度地沉迷于西方现代诗潮,而不免一时坠入一个极度晦涩的个人泥沼,所幸到80年代,台湾诗人开始自觉地由封闭的自我玄想向着现实世界开放,再加以对中国古典诗歌价值的再确认,回过头来向老祖宗学到不少诗的秘诀,而这些秘诀又是与西方的现代美学相暗合的。
至于说“40年代后,台湾诗歌走在大陆的前面,80年代后,大陆诗歌却走在台湾前面了”,前一句我倒是听说过,因为60年代初,台湾诗坛即全面拥抱西化现代主义,他们称“现代化是新诗的第二次革命”,而这时大陆正处于文革的体制化写作的禁锢中,“自由创作”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及到80年代大陆掀起了先锋诗潮运动,才逐渐回复正常的、个人的、体制外有效写作。两岸现代诗的起跑点相差大约30年。至于说80年代后,台湾诗歌落后于大陆诗歌,这个问题得看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如果就诗坛的生命活力和思潮涌动的强劲而言,台湾诗坛的确处于一种平稳,甚至停滞的状态。相较之下,6、70年代的台湾诗坛可热闹得紧,新旧对抗、中西交锋,笔战连年不绝,这种争论当然不可能得出一个摆平双方的结论,但却大大地刺激和强化了诗人的创作能量,我的一些代表作都是在那“诗歌战国”时期完成的。但80年代后,台湾的现代诗日趋成熟,在稳定中求发展,且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从此风平浪静,没有争论,没有任何新流派出山。于是诗歌的观念日渐僵化,诗人都缺乏一种内在的原创性,和自我突破的生命活力。
恰恰相反,近20年的大陆诗坛,自1986年“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以来,群雄并起,诗派林立,他们坚持体制外的民间写作,而成了另一种“主流”,从而使当代诗歌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气象,即便像“下半身写作”,或“垃圾意识”倾向(崇低),虽不是纯正文艺思潮的正常发展,但也代表一种反体制的、开放思想的存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台湾诗坛的确有些落后,不过话得说回来,大陆诗坛这种过度超前未必就是好事,尤其近10年来,大陆的经济突飞猛进,也带领起文化的繁荣,尽管商人不喜欢诗,但诗歌活动可激活商业的兴旺,于是许多县市都要办诗歌节,据说一个稍有知名度的诗人平均每个月要参加3-4项活动,有学术性的,也有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性的。活动占去了大部分阅读与创作时间。台湾诗人就安静多了,因此他们才能沉潜于 清醒的创造。我不妨在此提醒某些年轻诗人,表面的繁荣只是假象,每年至少要交出20部以上的优质诗集,才算是诗歌的盛世。
问:可否请您谈谈什么是现代诗?它的要素是什么?我们如何去把握现代诗意?
答:我只能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谈。50年代前我们写的现代诗,是以欧美现代主义的前卫(先锋)精神为标竿的,我们急切地吸取着现代主义大师们的理论,探索与研究他们那些象征派、未来派、超现实派的作品。他们认为:真正的诗人,只会按照他看到或者感觉到的事物来创作,任何文艺创作都是自发的、个体的,艺术家只属于他自己。神奇的事物就藏在表面看来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诗人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神奇的事物,他不但要写已知的世界,更要去发掘未知的世界。他力图使诗歌摆脱时空的限制,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反映个人内心独特的感受。
60年代我主编《创世纪》诗刊时,曾有系统地介绍欧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作品,也写过一些有关的评论,同事也进行了实验性的创作,长诗《石室之死亡》、《西贡诗抄》等即是实验的成果。十几年后我对自己全面向西方倾斜有了觉醒,开始修正“自动书写”的方式,而这种修正,正如前面所说的,却有赖于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入研探。我从唐朝大师们的作品中,居然发现了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后来我又惊喜的发现,超现实主义某些基本精神和表现方法与中国的禅宗有不少相通之处。于是我渐渐发展出一套我自己的,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修正超现实主义,这以后我写的大量的“现代禅诗”就是受此启发的。
经过长期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到了80年代,中国与台湾那些实验性很强的先锋现代诗已经逐渐有了变化,且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道路。台湾现代诗吸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日渐使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做了有机性的融和,最终生发出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歌,这就是“中国现代诗”,一种在美学观念上和表现手法上都远远超过五四以来的白话诗,而这时大陆则走向口语化、叙事性的发展,以取代对诗性语言、意象结构的追求,当然也有好的作品,但大多流于唠唠叨叨、口沫横飞的大白话散文。
现代诗意不仅是文字表面的意义,更是背后暗示出来的含意。所以诗的语言是沉默的,诗本身是一个意象世界,而这个意象世界是诗人所创造的。王国维说:“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辛弃疾说得更好:“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便无梅”,这说明陶渊明眼中的菊,林逋眼中的梅并不是现实中的事物,而是通过诗人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境界(即意象世界)。
我也常想,现代诗意可不可以用日常的生活语(口语),采用现实生活种的题材来表现?我想是可以的,新诗中确有不少诗意充沛的好诗,但诗从来不是世俗的,它的题材虽取自现实,但它成为一首诗时,必然要超越现实之外,譬如写鸟,有人这样写:
鹰是在战争中诞生的
在这之前
它只是一只鸟
“鸟”只是普通的小动物,“鹰”则是鸟类中的英雄,由平凡的“鸟”提升为一只不平凡的英雄,是要通过战火与死亡的熬炼的。这就是“凤凰涅槃”的意思。再看纪弦的《鸟的变奏》:
我不过才做了个
起飞的姿势,这世界

便为之哗然了
无数的猎人
无数的猎枪
瞄准
射击
每一个青空的弹着点
都亮出一颗星星
开始,“我”这只鸟即以不凡的姿态出现,接着十分简单地描绘了外在现实的危机,和一只鸟的宿命;最后两行轻俏的一个转折便把它沉重的命运升华为一种新的启示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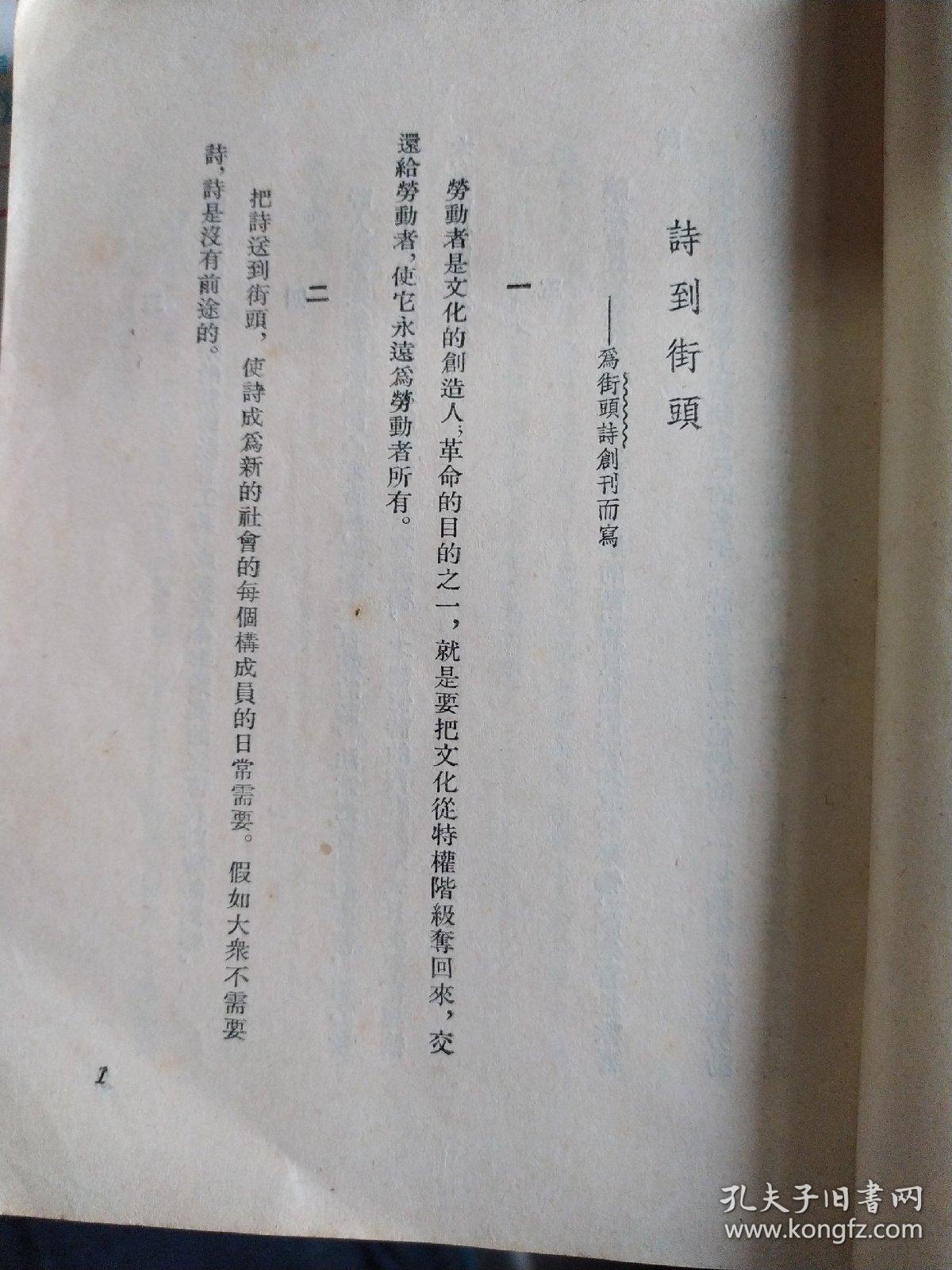
由此可见,现代诗意的捕捉不在于何种题材,何种语言形式,而在于如何营造一个富于想象的意象世界。
非马专题采访录摘抄
采访者:长篙
2-6、您认为诗歌在艺术、绘画、雕刻上的相互影响与意义?
非马:下面是我在一篇题为《学画记》的散文里说的话。为了免得重复,我把它抄录在下面:
诗同画之间最大的不同,我想是它们的现实性。诗所使用的媒介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语言。语言有它的约定俗成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诗(甚至文学)不能离现实太远。如果我在诗里使用“吃饭”这两个字,即使它们有比吃饭更深一层的意义,仍该多多少少同吃饭有关。否则读者会摸不到头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绘画不同,它所使用的媒介是线条及颜色。我在画布上涂一块红色,它可能代表一朵花,可能是太阳下山时的晚霞,也可能是一个小孩兴奋的脸,更可能是恋爱中情人火热的感情。所以我觉得绘画不妨比诗更超现实,更抽象。懂得欣赏现代艺术的人不会盯着一幅画去问它像什么?正如我们不会去问一朵花一棵树或一片风景有什么意义。只要它们给我们一种美的享受,就够了。当语言文字在一些感情面前吞吞吐吐甚至保持缄默的时候,绘画及雕塑便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及途径。而我发现,雕塑的随意性及自发性更强,更能满足我的创作欲。
2-7、简谈您主张的诗歌的形式和技巧;
非马:我曾说过:“诗是以最经济的手法,表达最丰富的感情的一种文学形式。诗人的任务是以最少的文字,负载最多的意义,打进读者的心灵最深处”。在这方面,中国现代诗应该可以从古典诗里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语言的精炼与准确。诗是艺术,任何成功的艺术都必须达到宋玉形容一个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那种恰到好处的艺术境界。

现代诗使用口语,但诗中的口语是经过筛选经过提炼的。它必须同内容密切配合。一首缠绵的爱情诗和一首有泥巴味的乡土诗所使用的语言与形式理当有所不同
新是所有艺术的首要条件。这个新不是标奇立异,而是在思想上形式上有所创新。别人或自己说过的话,如果没有超越或新意,便尽量避免。从表面上看起来平凡的日常事物里找出不平凡,从明明不可能的境况里推出可能,这种出其不意的惊奇,如果运用得当,常能予读者以有力的冲击,因而激发新的诗想,引起共鸣。
2-8、在《非马及其现代诗研究》一书中您对二度创作的定义如何理解,对修改后的作品与修改前的对照是否会产生歧义?
非马:一首成功的诗必须能对不同的读者,或对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心情下,产生不同的反应与感受。根据各自的背景与经验,读者可把自己的想像与解释加诸于一首诗,从而共享创作的乐趣。这便是所谓的“二度创作”。从这意义来说,一首诗必须有读者的参与及合作,才得以完成。
作品的修改是作者的内幕操作,读者一般只看到修改后的成品,应该不会产生什么歧义吧?除非是考察诗人写作过程的学术研究。
三、中国、世界诗歌的简述:
3-1、国内的主要诗坛各有什么特色?对诗歌论坛有什么希望和主张?
非马:我平时虽然也关注国内诗坛的发展,但并不是很熟悉,也没什么深入的研究。对于许多标奇立异的主张与派别,我都认为只是引人注目的手段,所以我一般都用比较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它们。我在一篇题为《铺天盖地话网络》的文章里曾说过下面这些话:“我想文学里有些东西是不变的,除非你不叫它文学。这些东西包括文学的固有特性及功能。诗人艾略特说过:“诗必须给与乐趣及人生影响。不能产生这两种效果的,就不是诗。”又说:“‘传统诗’和‘自由诗’的区别是不存在的。因为只有好诗、坏诗和一团糟而已。”我对‘现代诗’和‘后现代诗’(或文学)的看法也是如此。一个作家必须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命价值观以及对人文理性的信心,不能为了迎合讨好而去随波逐流,或玩弄时髦的新花样,制造一大堆浮光掠影、随看随丢的文学垃圾。另一方面,他也不该拘泥保守或局限自己。为了达到文学必须感动人并同读者沟通这个基本要求,他可以也应该‘不择手段’,包括利用有声有色、铺天盖地的网络。”
来自北美枫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