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许立志是一位年轻的诗人,他出生于1990年,广东揭阳人,曾被誉为打工文学接班人,而这位在诗歌作品中展现出相当天赋的诗人,却于2014年10月1日坠楼身亡。

关于许立志的自杀,坊间有许多传闻,就如同当年海子卧轨自杀一样,人们热衷于从各个角度去分析致使诗人自杀的原因,然而死亡一事太过神秘,活着的人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确信的答案。况且我们也不应当因为诗人的生死来评价他的诗歌,无论是过赞还是刻意贬低,都是对诗人的不尊重。我对许立志的诗歌印象最深的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这一首,我想从这首诗歌出发,谈一谈自己的一点肤浅的看法。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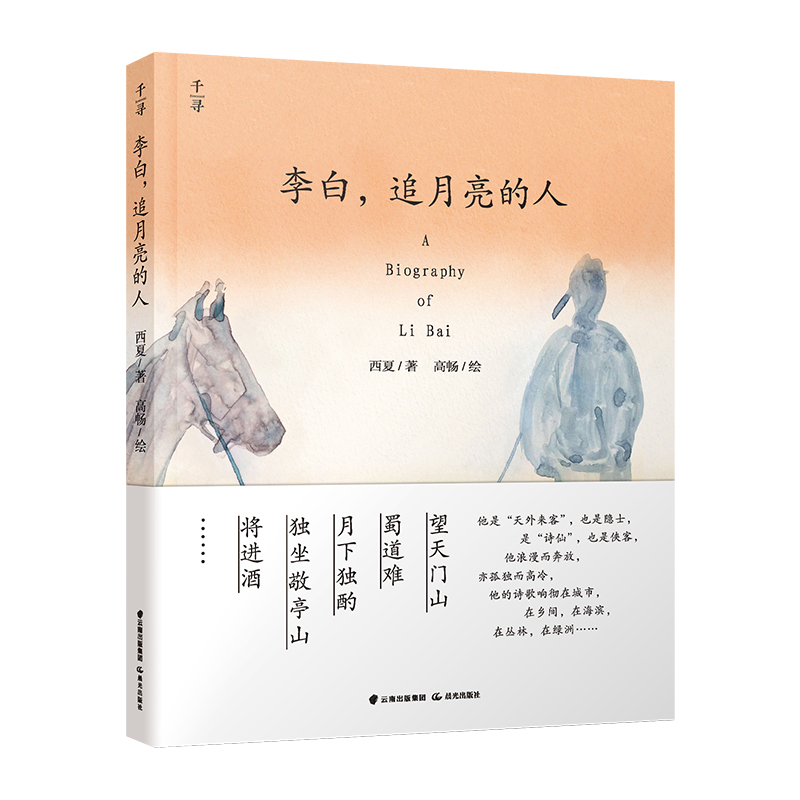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2013-12-19

月亮不再抒情
月亮作为一种经常在诗歌中出现的意象,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古诗词中描写月亮的诗句不胜枚举: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静夜思》是思乡的名句;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苏轼的《春宵》中,月亮做为背景衬托出了景色的清幽静美,同时也代表着时间的流逝,有惜时劝勉之意;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里,月亮仍做为背景,呈现了一副隽永优美的画卷,透露着思念之情。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张九龄的千古名句,意境雄浑阔大,想象力惊人。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则有一种含蓄哀怨之美。

在现代诗歌中许立志诗歌,月亮也常常代表着思念、爱恋等纯洁美好的情感,如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读来情意绵绵。 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明月在诗中代表了自然,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包含哲思而又有陌生梦幻之美。在海子的诗歌中,月亮出现的频率也不低,《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在这里月亮是高度凝练的抒情核心,除此之外还有 “黄色的月光”、“一只绿色的月亮”、“月亮是惨笑的白猿”、“月亮上我披衣坐起 身如水滴” 等等诗句。展现了诗人对月亮寄予的多种复杂的情感。
总之,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歌,月亮一直是一个高度抒情的意象。诗人常借助月亮来表达自己的思念、思乡、失意、哀愁等等情感,然而在许立志的这一首诗中,月亮是“铁做的”许立志诗歌,而铁是不具有任何情感属性的。诗歌的第二句:“他们把它叫做螺丝”,诗人使用了喻体前置,原来所谓的“铁做的月亮”,本体其实是一枚螺丝。
我们从诗歌的第一段就能感受到作者绝望、悲哀的情绪,原本在诗歌中代表着高度抒情的月亮无法引起诗人内心情感的共鸣,从“咽”字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诗人近乎生理性的痛苦,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诗人的这种认识呢?
月亮背面,满目疮痍
其实从螺丝这个词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诗人痛苦的根源。螺丝是步入工业社会才出现的一个物品,古代的诗人们拥有自然,可以浪漫地描绘风景,而在工业社会里,诗人却是待在流水线上,看到的是一个个毫无生命的冰冷物体。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类除了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 人们自身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创作的母题,即人的异化和物化。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最早表现这个主题的作品,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昆虫,家庭的厌恶和排挤令他绝望而死。
在这首诗歌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诗人所遭受的精神上的苦难,诗歌中没有任何积极的情感,诗人像一台机器一样咽下所有令他痛苦的东西。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工人们不仅承受着工业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也面临着被剥削、被拖欠薪资等生存危机,而在工厂夜以继日地生产着工业制品,为世界这个庞大的机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零件的背后,工 人们也变成了一个个僵硬的零件,在流水线上消耗着他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青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他的青春不是用来感受世间的美好,而是从事一种没有任何创造力的劳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残忍。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打工者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谋生,然而城市对待打工者并不友好,城乡之间的差距令打工者感受到了巨大的心里落差。打工诗人郑小琼曾在《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中写道:写下打工这个词/很艰难 //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飞腾的阶梯/但我抵达// 我把它读着陷阱/当着忧伤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苦咖啡/二年来/我让这个词横着/ 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
打工者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流离失所,却只能站在人行天桥上旁观城市的绚烂,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的生活长满水锈,举步维艰。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诗人或许经过了长久的忍耐,然而这种生活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诗人终于无法忍耐了,他所经受的磨难,曾经咽下去的所有屈辱和委屈,在某一刻终于爆发了。这并不是像酒后呕吐般单纯的排泄,而是把血和泪都呕出来,诗人称这是一首“耻辱的诗”,诗人或许感觉自己是无能的,没能得到更好的生活,但这不仅是诗人自己的问题,工厂主们,资本家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 我们是否是在为了每个人都能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月亮依旧抒情
我在提及月亮所代表的含义时,刻意没有提及它的另一个象征的含义,即: 永恒。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到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 月有阴晴圆缺,一时的亏损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残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月亮是永恒存在着的,我们所经受的苦难总有过去的时候,人类一定会有那么一代人能看到圆满的月亮。
打工诗歌/文学诞生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打工诗歌开始出现。最初打工诗歌以歌谣的形式存在,内容大多是对艰难的打工生活的调侃,随着打工诗歌的逐渐发展和一大批优秀的打工诗人的出现,打工诗歌走向了一个高峰。打工者们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悟,我想这就是诗歌的初心,就像《诗经》所传达出的思想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打工诗歌拥有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属性。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甚至时至今日,打工诗歌整体呈现出的面貌都是比较阴沉、消极的,这不是某一个诗人心里固执的想法,而是打工者整个群体的共同认知。在这些年里,我们通过媒体也能看到,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农民工薪资被拖欠的新闻传出,工人们在工厂中工作,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常常出现因机器致残的情况,何真宗在一首名叫《纪念碑》的诗中写过:
在南方/在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的缝隙里/我不止一次地从媒体上/看到类似的新闻--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地某街某处正在封顶的大厦/一个外省民工“不幸”/从楼顶摔下/一根或数根大拇指粗的钢筋/从其大腿臀部 斜插进肌体 穿肉而过/命根险遭不测……/经抢救/有的奇迹生还 有的永远 停止了呼吸 停止了工作/这就是我的打工亲兄弟呀/抛家舍亲/风餐露宿抽劣质 香烟/病了 喝一碗姜汤/背着铺盖卷四海为家/向一切需要力量的地方涌动的兄弟/汗水相当廉价/梦却又十分沉重/这就是我的打工兄弟/常常用自己的梦 装饰别人的梦/别人的梦 恰好成了他的纪念碑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这五类需求有如一座座大山般矗立在打工者眼前,打工者们需要一步步来获取食物、健康、住所、尊重、爱……生活真的很难!而诗歌像是来自天上的精灵,指引着诗人在这座金字塔间来回穿梭,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
从这一点来看,诗歌仍然是抒情的,这种抒情不仅仅是在一句一词中的情感抒发,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发声。在生活最艰辛的那一段时间里,是诗歌给予了打工者们内心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尽管对于许立志来说,他承受了太多,以至于最终导致了他的崩溃和绝望,但对于打工者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坚强的。自步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国家也积极地出台各项政策,致力于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人们所遭受的问题正在逐渐改善,未来将会是美好的,遗憾的是,总有人要为此而做出牺牲,就像许立志,他没能看到月亮的圆满,这是无情的时代选择。
所幸,他留下了他的诗歌。
在许立志的诗歌中,月亮或许不再抒情,但对每一个还在生活着的人,对向着未来的人,月亮还会走向圆满,月亮仍旧是、永远是抒情的。

